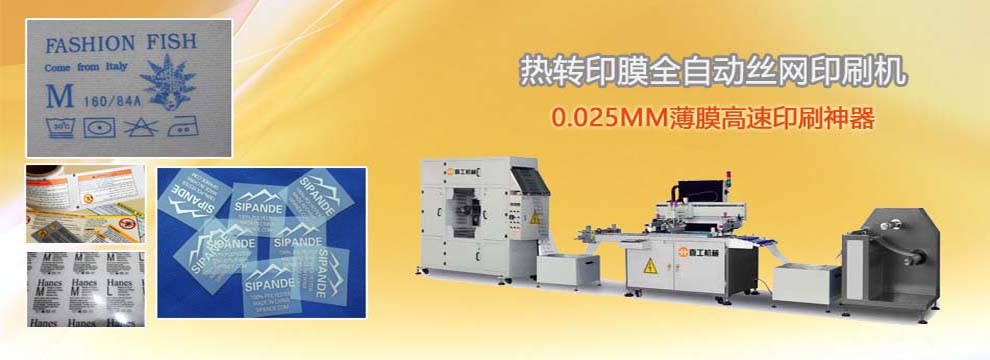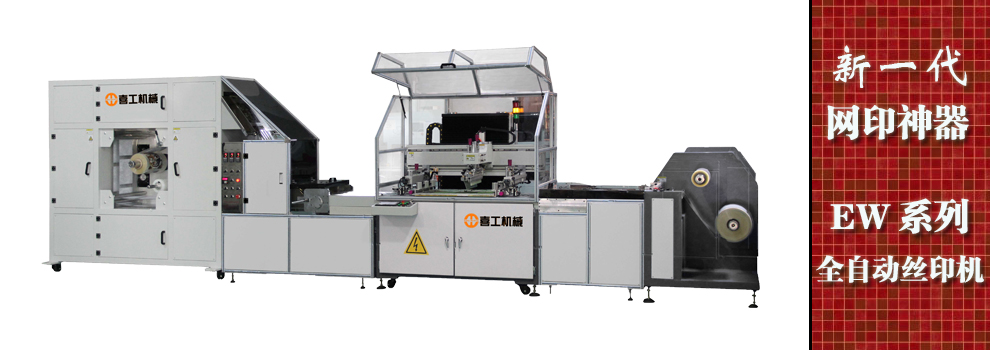和人類短暫的幾百年商業史相比,壟斷的歷史更加短暫——僅有100多年。在大部分的時間里,反壟斷政策一直處于一種尷尬的地位,壟斷和競爭的分界線時而水火不相容,時而模糊不清。反壟斷的呼聲也時而高漲時而幾乎處于一種默許的狀態。比如:微軟曾經在全球電腦操作系統市場擁有統治地位:將近90%的臺式電腦安裝了Windows,但是在那場眾所周知的世紀判決中他得以幸存。在歐盟,微軟的待遇卻完全不同,歐盟委員會在過去10年里向微軟征收了累計近20億歐元的罰款。
最近一家處在風口浪尖上的科技巨頭是谷歌。他在美國和歐盟的待遇也是冰火兩重天。2013年1月初,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宣布,確實發現谷歌通過某些手段以獲取競爭優勢,但是證據尚不足以說明谷歌違反了法律。聯邦貿易委員會和谷歌達成和解,對谷歌的反壟斷調查就此結束。在美國,谷歌占據了搜索市場份額的67%,其搜索廣告收入也占整個市場的75%。
但是4月份,歷經五年的調查之后,歐盟委員會對谷歌提起了反壟斷訴訟。該案的核心在于,谷歌是否利用其在搜索領域的霸主地位,讓自身的比較購物服務受益,令競爭對手處于不利境地,同時損害消費者利益。最近一項由哈佛商學院的MichaelLuca和哥倫比亞法學院的TimWu合做的研究發現,相對于完全按照相關性來呈現搜索結果,谷歌現有的做法使得消費者找到自己所需信息的機率降低了三分之一。一位歐盟的數字經濟專員聲稱,如果不采取行動,整個歐洲經濟就會因為對美國互聯網公司的依賴而面臨“風險”,甚至還有人呼吁要分拆谷歌。歐洲人使用搜索工具,10次中有九次是用谷歌。處于反壟斷漩渦的谷歌成立時間不過17年。
在中國,BAT三巨頭的壟斷地位早已不言而喻。2010年谷歌退出中國市場之后,百度獨步天下,占到搜索市場總收入約7成左右的份額。從交易規模看,阿里巴巴占據了中國網上交易額的80%。從某種意義上說,阿里一家把持著中國網絡入口流量的80%。將這些流量倒入金融,金融業會出現一個新阿里;將這些流量倒入旅游,旅游業會誕生一個新阿里。至于騰訊,微信的月活躍賬戶數達到5億,QQ的月活躍賬戶數達到8.15,約占中國總人口的6成。
互聯網的兩個經濟特征加大其壟斷的可能性
大不是罪惡,大也不違法,但是在西方的觀念中,大是對民主的冒犯。翻開反壟斷的歷史,其中所有的交鋒都是在做一件事:讓市場變得更具競爭性。只有當市場具有競爭性的時候,價格才能降低,市場會變得更加有效。美國有不少學者通過實證分析計算出了壟斷給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失。1929年,壟斷給美國制造業造成的福利損失占GNP的0.1%,70年代中期壟斷造成的損失在GNP的3%-5%。1985年,壟斷的社會福利損失占美國GNP的22.6%,這些研究得出的具體比例差異很大,但壟斷給消費者和整個國民經濟帶來的損失則為經濟學家普遍認可。
相對于傳統行業,互聯網所擁有的兩個經濟特征會加大其市場壟斷的可能性。第一個特征是其外部性,也叫需求方規模經濟,即用戶評估某個網絡的優劣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網絡上用戶數量的多少。也就是說,某個網絡的用戶越多,越能吸引新的用戶加入這個網絡,新加入的用戶會給網絡帶來正的外部性。比如谷歌,因為用的人多了,就有更多的人愿意用,這就是所謂的“贏家通吃”。以以太網發明人鮑勃•梅特卡夫的名字命名的梅特卡夫法則形象地說明了網絡外部性,即網絡的價值與其用戶數量的平方成正比。
外部性導致的結果是,如果企業不能充分地差異化,最后必然由一家壟斷市場,因為市場不需要第二家。無論是互聯網行業,電商還是共享經濟,任何一個細分市場最后都將是一家獨大。優酷和土豆的合并,58同城和趕集網的合并、滴滴和快的的合并,都印證了這個道理。
互聯網的第二個特征是供給方規模效應,即成本往往隨著銷量的增加而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從成本的角度看,由一家企業服務于整個市場是最有效的,這就是經濟學所定義的自然壟斷。但是,壟斷地位帶來的高價格又導致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合理,這樣就造成了悖論。對自然壟斷產業,政府一般從價格和市場準入兩個方面進行監管。一方面控制并壓低價格以防止壟斷價格的出現,另一方面提高進入門檻使得市場內的公司能獲得較大份額從而壓低成本。因此對于鐵路、電信、公用事業等屬于自然壟斷的行業,各國普遍對這些產業的價格和進入進行了管制,通常是只允許一家企業壟斷這個產業的生產。而最近由于Uber的進入而鬧得沸沸揚揚的出租車市場,也是屬于這一類別。
互聯網市場由于以上兩個特性,往往有很大可能出現自然壟斷。對監管者來說,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面對一個必然壟斷的市場,政府到底應該怎么辦?雖然某家企業把整個市場服務得很好,但是他的行為一旦偏離正軌該怎么辦?另外,如果我們對互聯網市場的自然壟斷屬性達成共識,是否也應像對傳統企業一樣對價格和市場進入進行管制?
除了壟斷性之外,互聯網的中立性(netneutrality)也是人們逐漸認識到的。2月底,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CommunicationsCommission,FCC)以3:2投票通過一項新規則,把寬帶互聯網作為一種公共事業來管理,這是網絡中立概念的核心原則。新規出臺之后,贊成者認為“FCC邁出了有史以來最大的監管步伐”。反對者指責這項新規“開啟了政府干預商業決策的大門。”
互聯網的中立性意味著基于互聯網的平臺類服務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公共物品的特征是可以在同一時間使多個個體獲益,典型例子包括國防、法律、廣播網絡、電視網絡以及鐵路等等。一個人對此類物品的消費不會減少其他人從該類物品中所獲得的效用。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的性質,即將特定的個體排除在公共物品的消費或使用之外,要么是不可能的,要么需要過高的成本。
如果中國監管當局也認可互聯網的中立性,那么政府是否允許一家企業壟斷互聯網的入口呢?比如微信。互聯網的入口不是一家公司的事情,而是屬于整個市場的公共產品,這就好比高速公路的入口不應該由私人公司把持是一樣的道理。
互聯網的自然壟斷屬性及中立性提醒監管者應該關注這個市場。但是在過去十年中,針對互聯網公司的反壟斷調查一直毫無進展,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現有的反壟斷法律對互聯網公司并不完全適用。壟斷的最終表現是定價權,而互聯網是免費的,價格為零。但是,壟斷僅僅是監管的必要條件,因為人們對數字壟斷還缺乏更深入和更透徹的理解。盡管在法律層面還處于觀察階段,但是對互聯網的監管應該盡快全面納入政府的議事日程。
監管的重心
“不治已病治未病”。如果說法律是給壟斷開出的藥方,監管當局要做的就是在壟斷已經初露端倪的時候,開始未雨綢繆。壟斷是一回事,濫用壟斷地位是另一回事。對政府來說,監管的重心應該放在后者。當一家公司擁有壟斷地位的時候,他很難不去利用這個優勢。以谷歌這家號稱“不作惡”的公司為例,在谷歌上搜索筆記本電腦,搜索結果是谷歌自己的一款對比購物服務,這便是濫用壟斷地位的不正當競爭。
那么,監管者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呢?相比傳統經濟,我們應該注意到互聯網的以下兩點不同。
首先,在互聯網時代,我們對資產需要更寬泛的定義。比如馬云說過,未來的能源是數據,這句話背后的含義是:數據就是一種資產,就是一種資源。谷歌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EricSchmidt)在2010發表的一份聲明顯示,谷歌在兩天內收集的數據大約為5艾字節,相當于從人類起源到2003年所產生的數據總和。對數據的壟斷就是一種數字壟斷,和對石油、鐵路的壟斷可能并無二致。
另一種資源是流量。當互聯網上的流量被少數幾家瓜分時,這也意味著這幾家公司可以利用這個資源來左右市場。比如,淘寶可以通過調整算法輕易地影響店家的銷售業績。而騰訊也曾利用其龐大的用戶群(也即流量)來輕易復制小公司的創新。如果像數據及流量這種核心的資源由于互聯網的壟斷性被少數幾家公司控制,很難防止市場不被他們影響。隨之而來的是消費者權益的損失,更不要說保持互聯網的中立性。
其次是對于整個價值鏈上利益分配的考慮。很多互聯網模式是通過資源匹配(如共享經濟)和削減中間環節(如平臺型電商)達到提高經濟效率從而創造價值的目的。但是當最終壟斷形成,我們發現大部分價值被壟斷者攫取了。例如淘寶在提高交易效率并讓顧客得利的情況下,自己也享受了超常的利潤率,而傳聞中大部分商家卻在虧損。同樣,雖然像Uber和滴滴這樣的專車服務通過匹配資源來提高整體效率,當他們最終取代了現有商業模式后并達到壟斷后,真的能讓顧客和司機分享到更多的利益嗎?這些都是未知數。那么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常用的監管手段,政府是否也應對利益分配進行直接的干涉?這也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
國際上有不少呼吁對互聯網公司網開一面的聲音,主要的理由有兩種:一是互聯網行業的進入門檻很低,競爭很充分,二是出于保護創新的角度,認為互聯網領域的監管必要性不及實體經濟。這兩種觀點看似有道理,但其實恰恰是忽視了互聯網的自然壟斷和中立性這兩個特征。雖然互聯網行業的進入門檻看上去不高,但是,不要說復制出一個BAT,即便再誕生一個新的滴滴快的,都是不太可能的。
當市面上充斥著關于企業管理新內容的著作,充斥著大量涉及企業生產力和效率的書籍,充斥著建立商業帝國的明星故事,人們對壟斷的關注就會越少,甚至會被視為一種不合時宜的主張,是對科技進步和企業家精神的攻擊。但是,如果壟斷不被約束的話,那些在競爭法則作用下自然歸于公眾的利益將會完全喪失。
反壟斷的目的并不是反對技術和資本,而是要求技術和資本得以平等地運用。反壟斷法尋求的是限制強者對弱者在公平競爭上的煩擾。對政府來說,在現在這個時點上沒有必要大動干戈,更不應該一棒子打死,而是應該保持警覺。一方面技術發展速度之快讓人猝不及防,另一方面在資本的推動下,創業企業的成長周期被快速壓縮。以滴滴快的為例,現在它處于燒錢的階段,試想一旦投資人要求其盈利,它很有可能利用壟斷地位行使壟斷權力,對司機和乘客兩邊都提取分成,而那時司機和顧客將沒有任何選擇。因此,監管最好的辦法就是引入競爭。
短短幾年,人們就已經生活在幾個數字壟斷者的陰影之下了。監管者應該看到,在互聯網的大部分市場上,壟斷已經形成,而且因為互聯網的自然壟斷等特點,一家獨大的局面將成為必然。如果政府還沒有觀察到這一趨勢,恐怕他們的思路已經落后于市場前進的步伐。正視這一趨勢,確保數字壟斷者遵守游戲規則,確保社會福利最大化,是監管的重心所在。
政府還應該意識到,以美國為例,在反壟斷的斗爭中政府并非贏得了每一場勝利。而且,對監管者來說,如何證明一家公司確實濫用了壟斷地位也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因為監管者和被監管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信息不對稱。
沒有哪一種力量能夠和技術進步的力量相比,但是,對技術的崇拜并不意味著理性的投降。正如19世紀末一位英國國會議員所說:“你能夠期望一家公司有良心嗎?它既沒有可供詛咒的靈魂,也沒有可以鞭撻的軀體。”(原文發表于福布斯中文網)